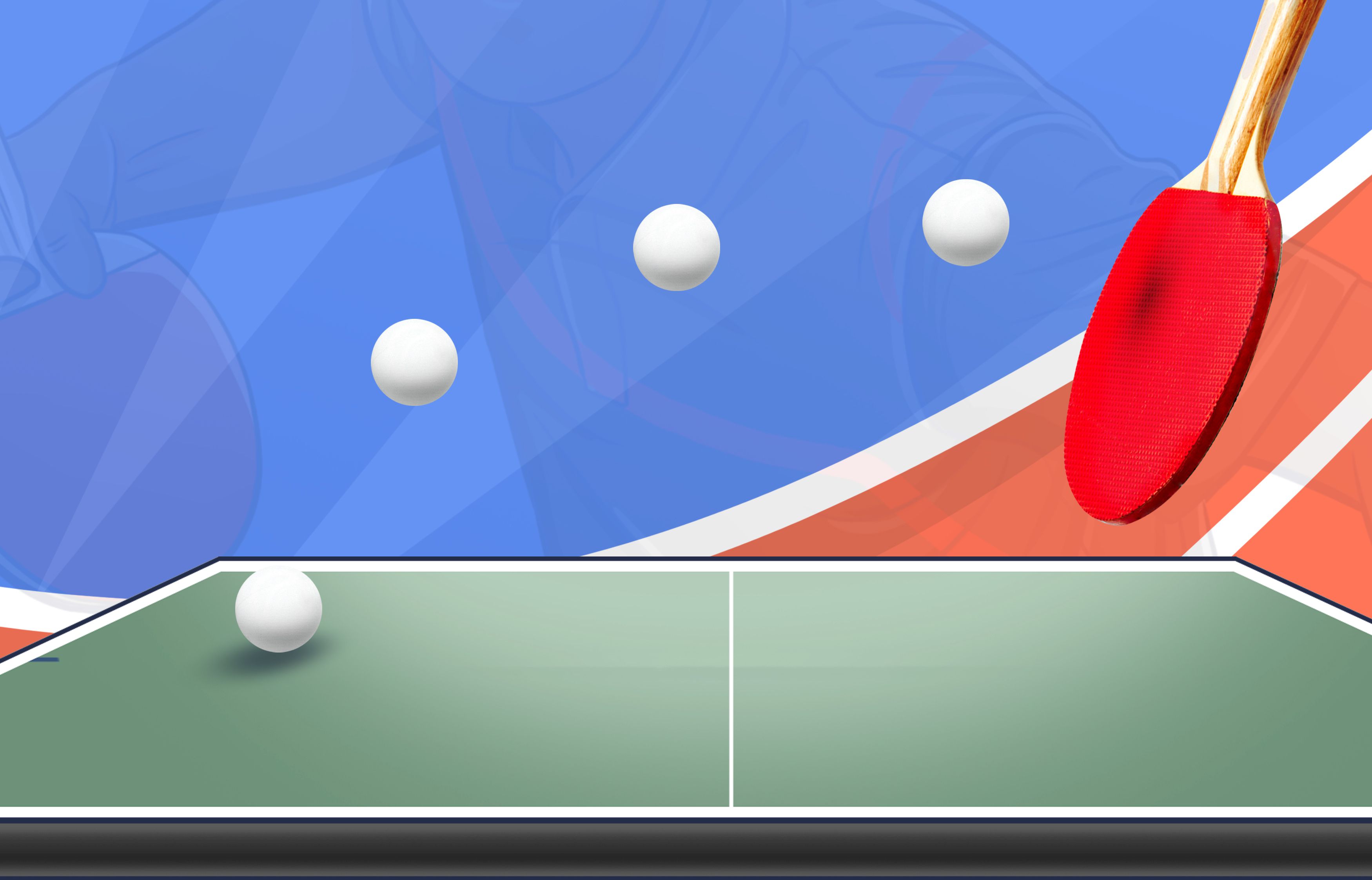(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公民个人信息权利受到侵害,私法层面是否具备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为人们所关注——
构建确保“诉之有效”权利救济机制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便捷的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个人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此,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规定的诉权以“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为前提,即设置了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置条件。笔者认为,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的理解和把握,需进一步延伸思考。
从立法层面看,在我国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处于“公法救济为主,私法救济不足”的状况。不可否认,海量个人信息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稳定息息相关,公法救济对于规范个人信息利用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公民个人信息权利受到侵害后,私法层面是否具有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同样为人们所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基础上,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具体权利,并明确相关权利的可诉性。实践中,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是否为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前置条件的理解存在分歧,这为个人信息主体行使诉权造成一定困惑与实际障碍。
理论上,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是否系起诉前置条件的理解,应从起诉权法定性、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割裂性以及法律体系解释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起诉权是法定的司法救济权,与当事人权利保障紧密相关,仅经法院形式审查即可发生效力,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排除或限制诉权的行使。而权利与义务具有不可分割性,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及其违反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应割裂看待,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应进行体系性解释。相较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民事侵权责任承担的普适性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仅是承接其第1款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构建个人权利实现机制之义务而作出的进一步规定。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的关系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的规定属于民法典的一种特别规定,其没有涵盖民法典所规定的所有权利人可以提起诉讼的情况。故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之规定不能机械理解。个人信息侵权纠纷法律规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未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出申请即诉至法院的案件,可以将信息主体未提出权利行使申请,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否具有过错的考量因素,在实体判决中予以体现,而非简单地裁定驳回起诉。
实践中,将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请求作为起诉的前置条件,可能引发更多的司法审查问题,如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拒绝应当作何理解,默示的拒绝是否可以视为已完成起诉前置条件,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表示拒绝但未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说明理由的情况能否提起诉讼,等等。对于上述问题不经实体审理,仅凭形式上的审查而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不妥当。况且,实践中大量用户协议既不被阅读,也无法真正获得用户同意,实际上变成信息处理者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合法”外衣,也不乏相关处理机制本身即存在妨碍用户行使权利的问题,或者个人信息处理者为个人行使权利有意设置种种障碍,导致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请求难以得到顺畅便捷的处理,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按照“申请为先,拒绝前置”的简单逻辑,将权利人拒之门外,那个人信息权利主体可谓进退两难。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视为起诉前置条件,不仅有违立法本意,而且不利于个人信息保护私法救济。对于个人信息权利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时,虽符合起诉受理条件,但未向信息处理者主张请求权行使的案件,法院可以在诉前调解阶段积极引导,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调解。如果诉前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个人信息处理者以对方未向其提出权利行使请求或权利行使请求仍在受理中尚未有处理结果为不具备过错的抗辩理由,法院应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角度出发,审查以下情况:协议约定的权利受理和处理机制是否“便捷”,是否存在不利于权利行使的具体内容;权利人是否事前知悉该机制的具体内容、其知情同意权是否遭受侵害,当事人对此种维权机制是否存在争议;平台在实际受理和处理权利请求过程中,是否存在推托迁延、设置障碍,实际造成维权困难;等等。在合理审查、依法判决的基础上,构建确保权利人“诉之有效”的个人信息权利救济机制,既能避免对个人信息权利主体诉权的不当限缩,也可反向推动个人信息处理者进行合规建设、改善优化权利行使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促进个人信息权利主体便捷地实现维权。
(作者分别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关键词: 构建确保诉之有效权利救济机制
- 世界百事通!构建确保“诉之有效”权利救济机制
- 今日快讯:脱身回国后,他立即去自首了
- 天天动态:绰号“小熊猫”却是黑老大 男子涉十二项罪名获刑二十五年
- 【世界热闻】私家侦探以调查为名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终获刑
- 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理解央行大幅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 交通银行交心存是理财吗?交银理财产品是正规的吗?
- 期货如何准确判断趋势?止损止盈设置技巧
- 【天天播资讯】国漫真的崛起了吗?腾讯披露数据,只看海外动漫的仅有这么多……
- 天天讯息:保护我方旺旺
- 环球时讯:游戏中报盘点:同比降、盈转亏占比过半,大厂靠长寿游戏吸金
- 今日快看!10天不足3亿,史上最帅《杨戬》,被自己“亲爹”毁了
- 环球即时看!微软揭秘史上最重的软件:高达 36 斤的 C/C++ 编译器
- 期货如何稳定盈利?期货盈亏是怎么计算的?
- 期货可以做到稳定盈利吗?期货可以做到稳定盈利吗?
- 环球热点!洋河股份投资成立餐饮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
- 通讯!ST众泰:在符合相关规定条件下 公司会向交易所申请摘帽
- 环球速递!格力地产:上半年归属股东净利润0.96亿元 同比下降79.56%
- 当前速看:尤安设计:2022年半年度净利润约-679万元
- 天天即时看!首旅酒店:上半年归属股东净亏损3.8亿元
- 全球实时:国盛证券给予兆易创新买入评级 Q2业绩高增 工业、汽车领域进展亮眼